吴江区老年大学81岁的同学张汝鸿写了一篇札记,记录了前不久她不顾年事已高,去千里之外的北京看望91岁的表姐的过程。那浓浓的亲情,暖暖的爱意非常感人。
张汝鸿和她的表姐是十年前回山东单县祭祖时相认的,此后微信传情,绵绵不断。从血缘关系来讲,她与表姐的DNA多说有几成的同源度,然而,即使仅几成同源度,就是一个“祖”字,也能使她们心之相通,念之有物。即使耄耋之年,亦有相思相聚之欲。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特别讲究的“慎终追远”要义所在吧,这是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信念和情愫。
在国人眼里,祖先从未走远,不只是泛黄史书里的一个名字,而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,是家庭餐桌上一个看不见的席位。“慎终追远”这个词,被无数具体的仪式所支撑。就像一把伞的伞头,伞骨蓬开能够遮住雨雪,庇护伞下人,但它有一头必须永远固定在伞头上。无论伞骨有多少条,无论伞布有多么华丽,没有伞头的聚集和主控,终将是一堆散落的材料。这也是中国社会有一种独特的风格,它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文明延续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,而这种风格,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学得来。
除夕夜,团圆饭开始前,很多家庭会在院内摆上贡品,点燃三炷香,口中念念有词,向先人汇报一年的得失。清明时节,无论城市化进程如何迅猛,人们依然会不远千里,回到故土为祖坟添上一抔新土。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——春运,便是这种向心力最直观、最震撼的体现。数以亿计的人,不惜忍受拥挤与疲惫,进行一场看似不理性的回归。驱动这一切的,往往只是一个极其单纯的目标:在除夕夜,赶回家吃上一顿年夜饭。这些节日,连同中元节和重阳节,共同构成了中国人与祖先对话的固定频道。
一些地方至今保留着祠堂或宗祠,那是整个家族的精神圣殿。而一本本厚厚的家谱,详细记录着家族的迁徙路线、成员的职业变迁、亲属关系的繁衍,它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家族史诗。对许多人来说,内心深处有一种强大的道德约束和朴素心愿,那就是“不辱祖先”。这种将个人荣辱与家族历史紧密相连的观念,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宗法制度。光宗耀祖的愿望,本质上就是向家族历史的交代,而家庭,也因此成为了连接渺小个体与庞大共同体的最基本、最稳固的单元。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,不仅关乎自身,更是在为一部延续了千百年的家族历史书写新的篇章时,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。这种源自家庭的纵向认同,最终汇聚成了更宏大的家国情怀。
一个“祖”字,有其强大的引力场。国人对“根”有着深沉的执念,那么,对祖先的敬畏则黏合了时间,跨越时空。许多人在外打拼一生,到了晚年,最大的心愿却是回到那个养育自己的地方,回到或看一看那个有“祖”味的地方。即便在城市化浪潮席卷的今天,许多人早已在新的城市安家落户,但清明返乡扫墓的习俗依旧顽强地存续着。这说明,故土不是一个地理坐标,“祖”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锚点。
这种情感,甚至被提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,有人将其比作“龙的逆鳞”,轻易触碰不得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引力中心,无数散落在各处的个体才不会变成孤立的原子,而是始终被一张看不见的网连接在一起。
这种强大的文化黏合剂,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不断裂、不失效。
我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,祖籍是河南省清丰县,一直到我退休后才第一次回到祖籍。当我看到祠堂里的家谱时,看到祖先牌位上前十二代姓什名谁时,眼睛湿润了,终于找到了我的根。尽管我不知道女儿将来能不能认可我的祖系,但我百年之后能在家族的体系中占有一位,起码证明这个世界我曾来过。在女儿生第二个孩子时,亲家母问我要不要孩子随母姓,我表示没必要,不要让孩子几辈后找不到祖宗,找不到他的根。在老家的那几天,血浓于水的感觉特别明显,心里庆幸,我60多年来,虽然没有做出可圈可点、光宗耀祖的业绩,但一直默默无闻的为国家,为社会,为家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,没有辱没祖先。
张汝鸿老师做为女性,在传统观念中对家庭祖系传承占在次要和弱化的位置,但她不忘出身,对“祖”的概念心有所系,注重亲情,弘扬正能量,十分值得敬佩和学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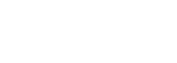
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
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
打印本页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