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案 此文获第十一届吴江区老年人文化艺术节征文比赛一等奖
开弦弓村因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赠予了“江村”的名号,由此闻名世界。这几年随着新农村的建设,乡村旅游也搞得红红火火颇有特色,忍不住想去看看。
想去开弦弓村去走走,另一个原因,那里有我年轻时的身影,七八十年代,乃至九十年代初期,每当这个时节,在农村夏收夏种的“双抢”时候,我们镇上的商业工作者,都要送货下乡,所谓的“送货下乡”就是送货到离镇比较偏远的村子,方便农民购物,那个时候,其实并不为了卖掉多少东西,更多的是政治任务,而开弦弓村是每年下乡必选的点,不仅是因为他处在庙港和震泽的中间,更因为那里的风俗与震泽的乡村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那个时候,骑着三轮车沿着碎石铺就的简易公路,要近两个小时才到达,老师傅们说,更早的时候要担担过去的会更慢。到了开弦弓的西青河桥边,这是开弦弓最热闹的地方,于是就像练摊一样,三轮车铺块板,摆上要出售的东西,我们是负责百货的,摆的自然是日用品,布匹服装。那个时候开弦弓的村里,年长的男的大都是对襟的短褂,下身是高腰的我们戏称“一二三”的连裆裤,年长的妇女都是斜襟盘扣蓝褂,头上包着蓝白色的毛巾,据说这是太湖渔民的衣着,这里濒临太湖,乡民既耕又渔。这古朴的民风,给年轻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在没有看到“开弦弓”三个字的时候,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叫“开源泾”更有在他们说要买“锥棍”的时候,更能体验到吴语的博大和复杂。
今天从震泽开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当年多次摆摊的西清河桥堍,今时震庙公路已修成宽阔的柏油路,桥堍的两边建起了几十家门店,小超市、小吃店各种店铺应有尽有,更少不了为游客一尝太湖湖鲜的小酒店,店铺的边上还建起了“江村集市”,时值“小黄蟹”“大头虾”的上市季节,集市里的玻璃柜,满满的都是它们,更少不了太湖的白鱼,银鱼,鳜鱼。集市的门口,和两旁店铺的门脸,都被装修成古铜色,颇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,俨然成了一个集市,成一个小小的古镇。
集市的南边,村里建了能容纳200辆车的停车场,往东就开弦弓村的乡村旅游的主题园“江村1936”里面有草坪烧烤、二十四节气栈道、乡土泥玩,比较有特色的是混水摸鱼、插秧体验、本来正是一个插秧的季节,很想体验一把,奈何今天的雨有点大,只能放弃。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,觉得比别的乡村并无二致,心中感觉缺了点什么。
园外的广场上,悬挂着乡村的变迁发展的图片和介绍,感觉“江村1936”的主题应该出自费老先生的“江村经济”这是费老第一次对江村的调查,而后的五十年间,费老从不间断的对江村的关注调查,发表了无数的文章,费老的文章是学术专著,我辈粗人,虽曾拜读,只是一知半解,但费老的“江村五十年”里依稀可见其脉络节点。
1936年是费老对江村的第一次调查,费老在“江村经济”的结语中说“饥饿是中国问题的症结”,“虽贵为人间天堂的苏杭乡村,大多数人民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”;1949—1957年,在解决土地问题后,无论是土改初期,还是合作社,费老说“农民的饥饿问题固然解决了,是生活的其他需要却无法得到满足和提高”;1981—1986年,在乡镇工业大发展的推动下,费老欣喜的看到乡村的农民才开始建房,农民走向了富裕,费老说“农村集体经济主干的乡镇企业,它的发展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实现的条件”。
而今距费老看到的江村悄然间又过了近半个世纪,身在其中的我们,也许并不感到变化,但猛然回头一看,足以令人为之一惊,费老说的要建的房屋,如今俨然是一排排一幢幢农家别墅;当年爱不释手的自行车,早已被一代又一代的新型汽车所替代,买个二轮电动车,只是为了方便上下班;费老心心念念的集体经济的副业—“乡镇企业”早已淹没在个体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,而今的村民早已不是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耕田者,而是流水线上三班倒的工人,有的成了企业老板,农民再也不关心农田里该种什么,产多少,计划交给种田大户,耕种交给农用机械。
养一些家禽,种一些蔬菜,不再是为了换一些油盐酱醋,而是为了尝尝自己的手艺,吃一些绿色食品。在这里我借用一下费老在“江村五十年”中的结语“历史的巨轮是不会停止的,江村过去五十年的变化,很可能是更大更富有意义变化的前奏,整个中国正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,”可以告慰费老的是江村后五十年的变化,正如费老所言在向更富裕更美好更强大发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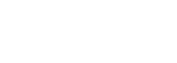
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
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
打印本页
